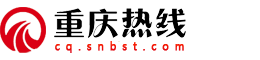译者要成为作者的捍卫者
来源:重庆热线 发布时间:2017-05-07 08:30
许多年前,读过王佐良教授的一篇译作:“读书足以怡情,足以傅彩,足以长才。其怡情也,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;其傅彩也,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;其长才也,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。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,然纵观统筹、全局策划,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。读书费时过多易惰,文采藻饰太盛则矫,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……”
我几乎没有想过这是一篇译作,它读起来那么“中国”。出于好奇,我找来了培根的原文,磕磕绊绊地看了,那种感觉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。把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,要忠实,还做到了本土化,这种难度几乎是无法形容的。
翻译除了艺术的一面,更有严谨、科学的一面。两种语言一定不是对称的,并不是中文里的一个词对应着外文里的一个词,这无疑让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。退一步说,假使语言是对称的,逐字翻译的句子也可能并不是作家本意。单就语言来讲,常常一个词、一个句子,就传递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观念。这需要译者对原文理解透彻,不仅要求极高的外语水平和母语素养,也需要对文化、历史等方面有广泛涉猎。翻译界有一句话:对外语的掌握水平决定翻译的下限,对母语的掌握程度决定翻译的上限。
我最喜欢的翻译,不是文学作品,而是一个化妆品品牌——Revlon。这是一个美国的彩妆品牌,中文译名叫做露华浓。这个曼妙的名字恰如其分,让人想起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。”同时它又关照着品牌的发音,可以说既是意译,又是直译,几乎是神来之笔。
中文每一个字都是语意和语音的独立单元,可以追求工整、对仗、平仄,可以写出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这样的神句。而印欧语系则不同,单词音节都是不同的,有单音节、多音节等。比如说李商隐的诗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几乎是无法翻译的,这四句中的平仄、音律无法转化成另外的语言,背后的深意更难以传递。同样,把“寻寻觅觅、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戚戚,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”翻译成外文,又是怎样的考验?
汉语和外语在语言结构、语言表现和语言习惯上大相径庭。同样内容的表达方式出入很大,这造成了理解的困难。可以想见,当我们的古诗词以其他语言呈现给外国读者时,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另外的东西,它承载着译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会有意外的惊喜,也无疑会顾此失彼。
听说,英国字典近年收录了“土豪”“大妈”这样的词,中国词汇逐渐被世界接受。作为世界上1/5人口使用的语言,中文的发展必然牵动着世界语言的变化。诸如 long time no see,geilivable(给力)也已渐渐走了出去。而网络语言、字幕组的兴起更是加速了汉语的发展变化。“大咖”“城会玩”“有钱任性”“累觉不爱”等流行语层出不穷,不要说翻译,生活稍微闭塞一点的国人都搞不懂其中含义。而且这些词寿命短暂,对于翻译来说更加难以把握。而如何把这中间的荒诞、搞笑、无厘头传达出来,需要译者跳出文本,对中国的社会、文化有深入的了解。
一位愿意把中国文学译介到世界的译者,本身就应该对中国文化富有兴趣。语言的变化和扩展再日新月异,文学自有它本身恒久不变的东西。细枝末节的变化,要服从于内核的不变。翻译难度固然会随着语言的更新而不断增加,但这是各个时代都一直面对的难题。
语言中细微差异的背后,常常是整个文化背景的不同。牵一发而动全身,所以很多东西是无法翻译的,更准确地说,无法直译。但也未必不能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。当我们认识到,一种语言无法点对点地转化成另外的语言时,我们依然需要阅读不同语言的文学,依然需要翻译。
我20岁之前没有离开过中国,然而阅读让我接纳了世界的丰富饱满。纵使在方寸之地亦可遥望无尽的远方,文字里突如其来的新鲜事远比生活来得酣畅淋漓。
我去世界各地度假,首先想起的是那里的作家。去捷克,布拉格各处都是卡夫卡的印记;去美国,那是福克纳和海明威的祖国,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小镇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,好像已经非常熟悉;去日本,在福冈街头找夏目漱石的故居,在河口湖,寻找太宰治住过的茶社。
我阅读并喜欢很多异国作家。写作本身就是跨文化的,一个人的视野、阅历、对世界的认知,经由作品被传递出来。文学作品具备超越种族、宗教、时空的力量。我最钟爱的三位作家,是塞林格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三岛由纪夫。他们都已谢世,但是我仍能轻易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共鸣。这一切阅读都仰仗着翻译文本。
我相信,翻译的过程难免损耗原作的一部分气息,这样的遗憾不可避免。但它也会增加新的东西,优秀译者的智慧也会为作品增加神奇的光泽。
(责编:左瑞、邓楠)
重庆新闻摘选